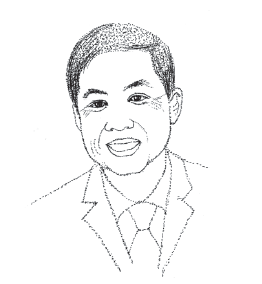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其核心所在,简单地讲,不是“占人便宜”就是“损人利己”。虽然说,“风险”只是指实际负面结果的一种可能性,如“财务风险”,仅仅表示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的财务实际损失,然而,“道德风险”却预示人们产生失德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确定性, 或者说,失德是大概率事件。当人们谈及“道德风险”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预计了一定会出现某种“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在公司治理中,究竟是什么会引起人们做出道德方面的负面选择呢?
观察表明,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公司固有的组织架构, 如业务条线、管理层级、部门或单元的设置划分等,它们分列出来了公司内部相对独立的一个个“小集体”。这种“小集体”终究是有自身独立利益所在的,一旦跨越条线、层级和部门的合作事项出现, 某些“小集体”就可能在付出有限的情况下,获得较多的好处,实际“占了便宜”。通常而言,“占人便宜”会分“有意”和“无意” 两种——前者涉及道德而后者纯属意外,“占人便宜”的动机是有是无,便成了问题的关键。有意思的是,公司治理中“有意占便宜”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也很容易看得出来,这类“道德风险”并不难判断。更有意味的是,因占的大多是“小便宜”,通常情况下,治理各方并不特别在意。
在固有组织架构之下的“损人利己” 之为, 也是时有发生的。不过,由于“损人”而始, “ 利己” 而终, 包含了恶意的算计和行为,其“损人”的过程就很难把握得住信息不外泄;而且,这类“道德风险”对于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有着非常明显的负面效应,为治理各方所难以容忍,因此,“损人利己”的事情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公司里,并不多见。尽管如此,这类“道德风险”却不能不高度关注,一旦它成势,演化出公司运转中的实际问题,那将是具有强烈负面冲击性的,甚至于具有毁灭性。
“道德风险”的另一个方面来源,是体制和机制的变化或调整。在某种既定的运行体制和机制下, 一家公司经过多年的内在博弈、磨合和相互适应,通常会达到整个公司一种累积型的“均衡”,各种治理的矛盾相对平缓和有序;而且, 由于内部机构与机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熟悉,导致程度较高的机构和人际关系的“透明”,“道德风险”容易识别而趋于最小化。然而,一旦体制和机制发生变化或调整,旧有的“均衡”被打破,相应地又会出现一些新的信息源和信息通道,形成某些信息壁垒;特别地,是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较大变化,驱动了新的利益博弈,“道德风险”便随之而来。细心观察一家公司的运行会发现,体制和机制变革时期,常常就是“道德风险”出现的高峰期。在严重的情况下, 许多的体制和机制变革最后无法完成,大多就阻滞在一些“道德风险”最后转化为实际负面的冲击之上。
基于新的利益博弈,又有信息不对称的环境,加上各种博弈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在体制和机制变革时,“损人利己”的“道德风险”就必定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通过对许多公司的案例综合分析, 事情的确如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任何一次公司体制和机制的变革,特别是那种“伤筋动骨”的改革,总是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代价; 而且,体制和机制变革总是会有反反复复的过程。
上述关于“道德风险”源起的两个方面,很明显,是属于外部的“外因”条件。当我们将视线转向“内因”,即驱动“道德风险” 产生的人的心智因素时,人性中某些本原性的规定,就凸显出来。这便是所谓的“人是自利的”或“人是经济理性的”(尚存争议)一类说法,它们在“外因”具备时, 就会蠢蠢欲动或是大显身手,将外部条件转化成自我的利益获取。如果说,我们将“人是自利的”看成是人性中无可厚非的本质规定, 那么,利用任何的外部因素来为自己获利,也就无可指责。相应地, “道德风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利益,就再正常不过了。即使是我们所说的“损人利己”,“利己”的自然合理性,也就决定了“损人” 不过是利用外部条件的一种利益实现方式而已,如果说那是“不道德”的,那也只能认为是外部条件“不道德”而非采取行动者的人。按此说法,“道德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合理的命题。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道德风险”的难题。
这个难题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迄今也没有一致的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存在着人性本质规定和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之间的直接冲突——认定人性天然规定“利己”的合理,那么,人出现任何“失德”之事,不关乎人,而仅仅是社会行为规范等不合理的问题; 相反,认定社会行为规范合理,人出现任何“失德”之事,那必定是人性天然规定就有“错误”。这个难题的实践困惑在于,两相矛盾之下,当遇到“道德”或“道德风险”实际问题时,我们究竟是应当去调整社会行为规范和外部条件, 还是努力去改造人性?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这样两种选择都实践过, 现在也仍然在实践之中。只是我们没有经常下意识地去思考而已。
从公司治理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公司,其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它的制度规范,因此,即使我们尊重人的“自利”本性,公司的制度规范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人性的基本规定必须受到约束而服从于公司的要求。“占人便宜”也好,“损人利己”也罢, 由于它们有悖于公司整体的利益, 违反了公司治理的基本规范,甚至可能危及公司的生存,这样的“道德风险”在公司治理中,是必须努力去消除的。换言之,公司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目标,容不得这些内部互相抵消、损伤和动摇根基的负面能量。
然而,人性在“自利”方面的顽固,在公司治理中,只要外部的“外因”出现,就必定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我们只能对引起它的“外因”下手,还是有可能痛下决心去尝试改造人性的“自利”规定,从而将“道德风险”驱逐出去?
公司治理的实践给予了我们某种有益的答案。在“道德风险”的应对问题上,许多公司倾向于根据不同的外部条件,进行不同的治理选择。
鉴于公司固有的组织架构具有不可消除的自然性,即任何公司都必定会有业务条线、层级和部门或单元的设置,由此而来的“道德风险”不可能通过取消内部组织来避免,许多公司就从人性的“内因” 入手,采取“企业文化”或“企业精神”的正面渲染,制定出道德行为准则,提升所有内部组织和个人的公司整体利益观,并给予优秀的组织、个人以“道德模范”的精神和物质激励,在张扬“非自利” 的人性光辉中,将“占人便宜” 的“道德风险”挤压到极小的空间;与此同时,一旦发现有“损人利己”的苗头,毫不留情地露头即压,防止演化成实际的“损人”之势,带来公司治理较大面积的负面影响。应当说,这种尝试去进行人性改造的“企业文化”之为,虽然“润物细无声”,实际的效果是值得称道的。看看那些发展得很好的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非常优秀的“企业文化”。
对于体制和机制变革引发的“道德风险”,治理的重点则放在考量这种变革是否现实可行之上, 即通过合适的变革范围、时机和节奏的确定,尽量不去激起新的失德行为产生。换句话说,治理者必须严格地把握这种变革,看其是不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公司“痛处”的基础上,条件是不是成熟,操作是不是成本可控;或者说,变革是采取渐进式的改良好些,还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革命更佳。通常而言,有了这样对变革设计、结构和程序的充分审视,变革的“度”就能够顺势生成,确保变革解决公司突出问题的同时,不会制造“道德风险”的副产品。颇具意义的是, 这种从“外因”来着手治理“道德风险”的选择,始终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适度的公司变革是好事,过度的变革则一定不是好事。
Visits: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