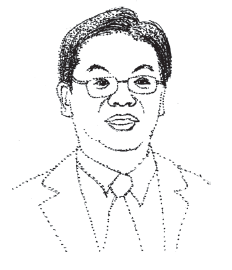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地理、民族、文化差异性都很大, 治理国家的难度极高。但是,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从未中断,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是怎样的国家治理智慧支撑起了这些辉煌的历史?
以民为本
古者有“四民”,分别是士民、商民、农民、工民,《春秋公羊传》解释他们的区别:“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通财货曰商。”从职业划分可以看出,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没有民,社会存在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同时,民还是国家赋税的提供者和国家军队的来源,没有民国家不复存在。
所以,从很早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历了夏、商、周的政权兴替,尤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大批诸侯国的兴起与衰亡,人们对君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更明白人民对政权的存亡也有制约作用,明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道理,所以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历代统治者都深知,国家政权要实现稳定,人民的生活必须富裕安康, 如管仲所说: “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 话说得虽直白,却是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以孔子也说:“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则说:“足国之道, 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刘安在《淮南子》中就此总结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历代以来,凡想有所作为的帝王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的道理,其在位时都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强国富民。汉朝初年,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立即减轻田租、豁免徭役、复员士兵、释放奴婢、鼓励生育、与民休息。汉武帝时又大兴水利、移民屯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唐朝初年,唐太宗、唐玄宗积极发展经济,开辟土地、推广水利技术、发展手工业,使经济达到新的繁荣,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富民离不开利民、惠民,要让经济繁荣的成果惠及百姓生活。西汉初年一直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后来更降为“三十税一”, 唐朝初年强调税收政策的公平与合理,通过“检田括户”等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偷逃税收的行为,减轻广大百姓的负担。清朝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其间五次大规模蠲免全国钱粮赋税。
“以民为本”几乎成为中国历代以来统治者治理国家共同坚守的基本指导思想,除了富民、利民、惠民,还强调顺民、敬民、护民、恤民。虽然很多时候其出发点或许只是为了借此来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但相关思想和国家治理理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法互补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法家更专注治国之道的探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国思想,其中儒家更强调民意,而法家更强调效率。
儒家强调仁政,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孔子提出了天命观,主张“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孟子对其进行了发展,认为民心即代表天意,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主张“以民心而察天意”。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对其改变和塑造。梁启超评价:“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在治国理政中,儒家主张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来稳定社会,主张为政者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引导民众建立思想道德规范,所谓“其身正, 不令而行”,同时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体恤民情、善待百姓。
儒家治国思想中有浓烈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强调个人的修为和人的自觉,也描绘了美好的图景,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但是,儒家治国思想中也存在理想化的一面,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设和“礼” 的约束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中的所有问题,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时,德治、礼法在效能上往往显得不足,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加以改造。
法家对儒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与强调仁、德、礼的儒家不同,法家强调法、术、势,强调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商鞅提出“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所谓“势”,指的是一种力量,是权势和威势,强化“势”就是更注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效率。韩非子说“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 他认为用忠顺孝悌之道治理国家效果并不好,主张必须用“法”, 提出“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 群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法家强调以“法” 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战国中后期,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分别在魏国、楚国和秦国实施变法,除强调法治外,他们还提出废除井田、重农轻商、实施耕战、奖励军功等改革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在战国诸雄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了天下,显示出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效力。但是,秦朝建立后又很快灭亡了,其速亡的教训也引发了人们对严刑峻法能否带来长治久安的反思。
汉朝建立后一度实行“黄老之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但在具体治国方略中,汉武帝也借鉴了法家的许多主张,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等。到了东汉末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国家陷入战乱,儒家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曹操在治政方面“揽申、商之法术”“不官不功之臣, 不赏不战之士”,法家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在此之后,历代治政者对儒家和法家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唐朝重儒家,但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宋朝时,儒家地位进一步上升,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更偏重于法家。
隋唐以后,治国思想越来越呈现出儒法互补的局面,有人称之为“王霸杂之”,有人将其总结为“外儒内法”,这种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是将尊顺民心民意与追求治国效能有机的统一,通过二者的深度融合互补,使法家的法治成为儒家善政的制度保障,使儒家的德治成为法家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 从而避免了只强调其中一项所带来的偏差。
乡村治理
中国有广阔的地域空间,除了思想、文化、制度层面有很大的整合和治理的难度外,单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也极为不易。古代交通、通信手段原始落后,因技术原因而导致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为克服庞大国家的治理困难,中国历代王朝探索出许多有效的措施,独特的乡村治理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的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 乡村是血缘宗亲与有限地域范围内的共同体,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 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来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古代的乡绅来源很广泛,既有卸任回乡的官员和暂居乡里的官僚,也有无官无名但在地方上素有威望的乡里领袖、宗族长老,他们不入官职品级,但在协调上下关系、维持地方安定、化解矛盾冲突方面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秦朝到唐朝以前,中国乡村普遍实行“乡亭制”,乡亭人员虽属官派,但利用民间力量的协助是其不可或缺的治理途径。唐朝设立里正,乡一级组织虽然还在,但里正发挥的作用更大。宋朝以后“保甲制”开始施行,保甲、乡里并存,但乡里的作用越来越弱化,保长、里正等乡村本土人士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农民之间产生矛盾往往不是去官府诉讼,而是依靠本地有名望的乡绅调解。基于这种特点,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依靠乡绅治理乡村,不仅可以强化宗族观念和儒家思想,从而凝聚乡村力量、维护乡村秩序,而且可以减轻治理成本、解决广大基层难以治理的技术难题。从秦汉建立三公九卿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各代的管理体制不断充实和完善,但官员的人数却总体上保持着较低水平,清代学者刘献亭在《广阳杂记》中统计:“汉光武时,省官止七千五百余员;唐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余员;明洪武初,武职二万八千余员。”虽然该统计未必完全精确,但大体反映了这些时期官员队伍的规模状况,上述数字肯定不包括服务在广大乡村的吏员和乡绅,否则总数恐怕会增加数倍、十数倍不止。
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中国也屡屡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无论外敌的入侵还是内部浩劫,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治理方面也如此,但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去看,那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和模式也许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辉煌物质文明与璀璨文化基于此而产生,中华文明未曾中断、中国“大一统”王朝始终持续也得益于此,它是古代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 我们对此应充满自信。
Visits: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