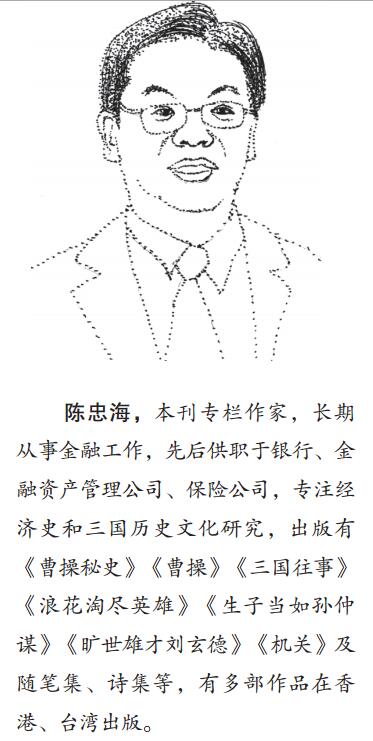陈忠海
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存在专门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人,“职务消费”就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这方面也早有许多制度和规定,并把抑制过度“职务消费”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但成效却并不理想。
职务补贴
古代官员的收入习惯称俸禄,按最早的含义,它包括“俸资”和“禄米”两部分,“俸资”是钱,“禄米”是粮食,这是因为早期官员的收入经常以货币化和实物结合的形式发放,如汉代就实行“半钱半谷”制,宋代以后官员收入才以钱为主、以粮食为辅。
考察历代官员的俸禄情况,薄俸是基本特征。东汉一名百里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这些钱只能养活两个人和1匹马。晋朝官员的收入也很低,晋武帝说“今在位者,禄不代耕”。元代一名九品官“一月之俸,仅了六日之食”,明代一名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这些收入要折成钱和米发放,称“折色”,最后能拿到手里的是12石大米和27.5两银子,靠这些只能穿布衣、吃糙米过日子。
但俸禄只是官员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在俸禄之外往往还有很多补贴。魏晋以前没有品级制,但很多官员都有爵位和封地,在封地内可享有一定户数的食邑,如“万户侯”就是享有1万户食邑的侯爵,拥有爵位者可以“衣食其租税”,这是官员俸禄的重要补充。
魏晋以后官员品级制逐渐固定下来,食邑封爵成为一种荣誉,官员职务补贴以其他形式发放。隋朝开皇九年(589),朝廷颁布诏令给京外的官员发放公廨田,后将这项制度扩大到内外各官,其中在京的官员按品级不同发放公廨田2至26顷,在外的官员发放1至40顷,公廨田出租后取得的收入“以供公用”,其实是一种职务补贴。
唐朝官员的收入结构后来又进行了多次调整,形成了授田、赐禄和俸料相结合的体系,俸料包括月俸、料钱、杂用等项目,其中料钱专门用于公务支出,这部分在官员全部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重。
宋朝官员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等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公使钱,也是一种“职务补贴”,发放标准视官员品级高下而定。到明朝,各地方在正常赋税之外增加收费的现象十分普遍,海瑞任淳安知县,该县每年正税仅925两,但前任知县每年却收12950两,各种“乱收费”是正税的十几倍,正税上交国家,多收的往往就以各种补贴和办公经费的名义发放了。
清朝推出了公费和养廉银制度,主要用于官员的生活补贴和衙门的日常运作,这些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超过了正常俸禄,有学者研究,在清朝汉族官员的固定收入中俸禄只占22.2%,养廉银占68.3%,公费占9.5%。
公务招待
“职务消费”里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务招待。
早在周朝就设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兽人、渔人等,负责承办重要聚餐活动。自周朝开始,每年元旦都会举办正旦宴,不仅臣僚参加,有的还允许带上家属,冬至、寒食、重阳等重要节日朝廷也会举办宴会。此外,皇帝登基、过生日等也都会举办宴会以示庆贺。
官员私下里的迎来送往也很频繁,《汉书》记载:“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后汉书》记载:“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这种迎来送往的风气到南北朝时甚至得以“制度化”,当时有“送故”的潜规则,即官员上任或离任时所在地方都要送礼,其中离任的官员原任职地每年都要派人去送礼,时限一般为3年,为此有些州郡干脆设了个“送故主簿”,专门负责这件事,“饷馈皆百姓出”。
唐朝官员升迁要专门摆一桌“烧尾宴”,其名称的来历,说是人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就像猛虎变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将其烧掉。这种宴会极为奢华,唐人韦巨源举办“烧尾宴”的菜单保存了下来,菜品包括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以及面点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为盛大,费用多由公款支出。
唐朝以前官员没有“工作餐”,但有类似做法,《国语》记载:“楚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唐太宗李世民“克定天下,方勤于治”,规定官员上朝的时间不仅更早而且常延时,于是命人在宫殿外面的走廊里“聊备薄菲”,等于一顿工作早餐。到宋朝这项制度固定下来,不仅朝臣可以享用这样的餐食,一般官员也可以,称“廊餐”。元、明时也都实行这种制度,明朝官员就餐的地方一般在奉天门或武英殿。清朝时,有很多官衙干脆办起了“机关食堂”,清人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记述了某河务机构开办的食堂,“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场面十分盛大。
除了“工作餐”,官员们还经常有其他聚餐活动,宋朝有“旬设”的制度,官员每个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费用从公使钱中支出。宋朝政府还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从制度上给公款吃喝开了绿灯,所以宋朝官员大吃大喝的情况较为严重,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中,庆历三年(1043)西北地区的渭州每个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记载。
这种情况到清朝越发严重,《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任陕西督粮道,西安时称“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从这里过。张氏记述,“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当时大鱼每尾要花费4、5千文,其他还有白鳝、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在任陕西督粮道期间,张氏感叹“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算下来接待费“每年总在五万金上下”。
公款旅游
古代交通不便,诏令、公文以及信件传递成为问题,官员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于是国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
秦汉时驿站制度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到唐朝驿站体系达到了完备,在全国主要交道要道上每30里就有一座驿站,据《通典》统计唐玄宗时全国有驿站1639个。宋朝的驿站制度更为完善,从功能上将其分为邸、馆、驿等。元朝驿站称“站赤”,明朝对这项制度更重视,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全国驿站,把“站赤”重新改称“驿”,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对驿站的接待标准进行细化,全国涌现出河间府的乐城驿、东平府的太平驿、扬州府的广陵水驿等知名驿站。
古代官员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务的同时也喜欢寄情于山水,驿站成为他们“半公半私”的游历工具。唐朝盛产诗人和散文家,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诗人、文人,写了大量歌咏各地山川名胜的诗文,如果没有官府驿站,他们的足迹很难涉足这么广。韩愈在诗中说“府西三百里,侯馆同鱼鳞”,白居易写“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音五十里,已不属苏州”,可以看出驿站分布之广。
靠着发达的驿站,苏轼的足迹西到陕西凤翔、东到江苏吴江、北到河北宝县、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明清以后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
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与驿站有关的作品,李白的《题宛溪馆》、王勃的《白下驿饯唐少府》、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还出现了“题壁诗”,学者王子今把这种“泥墙墨书”称为“文学史的特殊视屏”。
清人查慎行从北京南归,沿路经过各地驿站,一路走一路写,写完就题在驿站的墙壁上,一趟行程下来竟然有60首诗,刊刻一册为《题壁集》。不仅相对短小的诗词,大段的文章也有人题写在驿壁上,如李白的《姑熟亭记》、柳宗元的《馆驿壁记》、刘禹锡的《管城驿记》等,唐人孙樵的成名作《褒城驿记》也属这类作品,被称为晚唐文学的代表作。
积弊难改
但是,除了方便文人们诗酒唱和、纵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费旅游所带来的却多是弊端。
《清稗类钞》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个叫钱豁五的惯骗,有一次要从广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里,路费是一笔大开支,他想到了官府驿站。钱豁五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其实明清时驿站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想混进去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还要出具勘合,相当于工作证和介绍信。勘合本是专人专用,但由于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卖了或送人情,也有人伪造勘合占便宜。
这只是被人钻了制度的漏洞,而相关制度所产生的浪费和腐败更让人惊心,仍以驿站为例,其经费支出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成为一个巨大包袱。《明会典》记载,张居正改革期间整顿全国驿站系统,仅精简了1/3就省出94万两经费,而当时户部每年的库银收入只有300万两左右。

再说公款吃喝,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难治理,汉景帝时出现了连年歉收的情况,但官员们公款吃喝依然很厉害,汉景帝不得不下诏,发现谁接受公款宴请一律就地免职。汉宣帝时有官员出差期间招待费过高,奢侈浪费,朝廷曾下诏进行过“通报批评”。宋朝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公款招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官员需凭“券食”方可用餐,类似“就餐券”,用餐标准也有规定,超标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发挥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制度事关执行者的切身利益,那执行效力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改变。最高决策者无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通过制度约束让官员们保持克制,但这种约束往往是无力的,抓得严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弹。
说到底,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关,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人与人不是通过制度、规则而是习惯于通过私人关系发生联系,人情大于法治、大于制度,“有人好办事”“只要有人没有办不成的事”等观念自古就很盛行,于是人们在维系各种关系上愿意花费更大的精力和资源,从而把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Visits: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