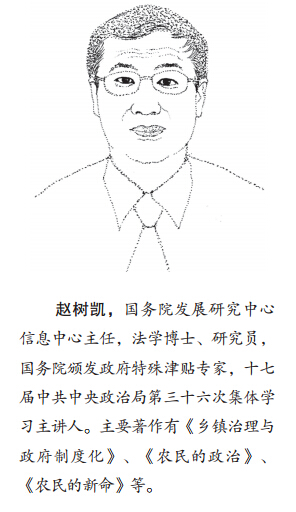赵树凯
直到现在,外界都在说纪登奎在九号院是“正部级研究员”。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比较符合纪登奎晚年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的实际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这个说法的正式依据。
记得有一次开会,秘书处要编印会议人员名单,我们不能确定纪登奎的职务如何填写,就请示一位副主任,得到的答复是:就写“正部级研究员”。纪登奎看到名单后,虽然没有表示不悦,但是并不认可,他说:“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正部级。”他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认为自己已经被明确“降级”,即从过去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降为正部级。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自己仍然是“副总理级”或者现在说的“副国级”。那么,他是什么级,其实很难说清楚。在这里,我试图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描述纪登奎晚年的“待遇”状况,或者说,呈现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遭到某种贬黜后的生活状况。
干部待遇是这个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史研究,中共干部待遇体制自延安时期逐步建立,是任弼时担任五大书记之一时主持设计的,建国以后这套制度逐步严密和完备。从基本制度框架看,不论是“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的现在,没有大的变化。高级干部的待遇基本上可以分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两个方面。构成生活待遇的基本要素有:工资、住房、医疗、用车、生活特供等;构成政治待遇的,主要是收阅党内文件的层级和会议活动。大致上,能够从这种种待遇观察推测一个人的体制内地位。
(一)
我并不知道高层关于纪登奎晚年生活待遇是如何规定的,但是,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可以大致上描述他的生活待遇概况,从而可以探测高层领导人失势后的生活状况。
如果是现在,很容易从工资看出级别,因为现在的工资是与行政级别直接对应的。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是这样,因为行政级别是和工资级别分开的。如一个干部的职务是副部长,但是他的工资级别可以比一个老处长还低。因为工资待遇和职务级别没有内在联系,从工资无法判断他卸任后的真正级别和待遇。纪登奎的行政级别是九级,当地委书记和副总理的时候,工资都是拿九级工资,每月230元左右。纪登奎的工资关系不在九号院,每月领工资是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当时,九号院里的高级干部中,有三个人工资关系在外单位,除了纪登奎以外,还有从林业部常务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杨珏,从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武少文。这两位部长为什么工资关系没有转来,他们自己说为了退休还回原来的部里,因为这些部委的待遇条件更好。当时,高级干部工作调动并不转工资关系,情况是比较多的,连他们的司机、秘书也有这种情况。在工资之外,不同的中央机关,对于高级干部的待遇条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并没有正式的制度规定,主要依据这些部门自身的条件。1990年九号院撤销时,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基本上都被农业部接管。但是,中央办公厅曾专门通知,张平化、张秀山、杜润生不必退到农业部老干部局,可以转到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部门。这三个人都曾是中顾委委员,行政级别分别是五级和六级。据说中办对老干部的照顾更好。后来,张平化、张秀山都转到中办了,杜润生则表示不愿意离开农口,不到中央办公厅,继续留在了农业部,成为农业部的退休老干部。
纪登奎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时,住在西单附近,是一个有独立院落的二层楼,家里驻有一个班的警卫人员。1980年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位后,搬到后来的住房,是内务部街一个四合院。这是过去清代大太监李莲英的住房,华国锋任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时曾住在这里,但是华国锋当时住的房子更多。纪登奎说,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再住原来西单的房子。这个院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居住,后院主要住工作人员。这个院落的北面是正房,东西各有厢房,正房和厢房还有耳房,约有二十来间。显然,这所房子不如原来西单附近的房子,但明显高于一般部长级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级干部住房,部长基本都住在单元楼里,一般五六个房间,面积一百八九十平方米。当时国务院系统的部长宿舍,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木樨地22号楼和24号楼,九号院里杜润生等几个领导也住在那里;党中央系统的部长宿舍,比较集中的是万寿路甲15号,朱厚泽、王郁昭等来京后住在这里。纪登奎家里还有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出的厨师。根据内部规定,部长级干部家里没有厨师。住这个房子是要交房租的,纪登奎在世时这个院落的房租每月是五十元,从工资里直接扣除。纪登奎家里没有通常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
根据内部规定,高级干部去世以后,遗孀可以继续居住原来住房,遗孀去世后,原住房将被收回,居住在其中的子女则被另外安排。对于子女住所的另行安排,通常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过程,即用多少公寓房来换取家属同意搬离原住房。纪登奎去世不久,夫人还健在,有关部门曾经商谈过退出原住房的事情,但是因为另行安排的住房家属不满意,没能协商好,就继续住了下来。2011年夏天,纪登奎夫人王纯去世。现在,这个房子还继续归纪登奎子女居住。有关部门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让纪登奎家属搬离,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一般情况是,领导人夫妇均去世以后,原住房会比较快地被调整安排,别的领导人要搬进来居住。如果有了新的安排,有关部门就会在谈判中让步,会尽量多给子女住房,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据说,有一位领导人夫妇都去世后,子女继续居住在中南海附近的一处院落里,经多次谈判,其子女都拒绝让出这个院落。而此时,这个院落已经安排了一位现任的中央领导人将要搬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实行了强制搬离。也许,有关部门之所以没有急于让纪登奎家属搬离,是因为尚无领导人需入住这所房子。
纪登奎当时有一部专车,是进口的日本车,并配一名专职司机。司机老张是他在位时候的两位司机之一。纪登奎离京外出坐火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安排一个软卧包厢。从这种交通条件的安排看,基本上属于正部级待遇。按照规定,正部长可以一个人住一个软卧包厢,相当于四张软卧车票,同时,随行工作人员还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坐软卧,即另买两张软卧车票。换一个说法,即一个正部长外出乘火车,按照规定可以报销六张软卧票,也就是一个半包厢。当时出差,纪登奎愿意我们与他坐在一个包厢里,只用了四张票。这样,就不必另买工作人员车票。如果是副部级乘火车,则只能报销本人一张软卧票和一位随行人员的软卧火车票。副总理外出坐火车,按规定是乘坐“公务车”,即在某列火车上单加一节领导人专用车厢,车厢里有办公室、休息室、会客室,还有随从人员包厢。纪登奎的司机老张经常与我聊天,他说原来是他当副总理时的司机,那时候是配备了两辆车,两个司机;另外,家里还有一辆生活用车,主要是工作人员办家务事用的。
来到九号院的时候,纪登奎已经没有警卫员。按照规定,副总理享受二级警卫,是有警卫员跟随的。如果出差,副总理级别的官员不仅有随身警卫,而且有关保卫部门也会派出人员负责沿路的警卫工作。就二级警卫的一般要求来说,通常在路过的主要交通路口要安排执勤人员,在宾馆下榻时通常会要求所住楼层实行封闭。一级警卫则有更高要求。从我陪同纪登奎出差的情况看,北京方面没有派出任何警卫人员。到了地方以后,省里安排了警卫人员,但是,我以为这是地方考虑到他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才安排了警卫人员,而不是因为有规定性警卫要求。另外,外出中食品安全检查也属于警卫范围。按照规定,副总理级别的外出吃饭,需要有专门的食品安全检查。记得有一次地方宴请,席间上来了娃娃鱼,这种鱼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陪同的省委常委兼农工部长说,上年赵紫阳来了拒绝吃,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的规定,作为总理不能带头违反。纪登奎则说:“我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你们既然做了,那我就吃。”
按照规定,副总理以上领导人有生活用品的特殊供应,一般叫“特供”。部长级干部没有这种待遇。纪登奎退出现职后,依然享受生活特供。特供是以食品为主的生活用品。在贵州遵义时,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两瓶茅台酒,我告诉他后,他开始说就不要了,对我说:“我不要了,你都拿走吧。我的特供里有茅台。”因为他有“特供”,每月可以从特供点买两瓶茅台。后来在回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又说到茅台酒,他说他的孩子们有时候常为这两瓶茅台酒争执,他的孩子有时候要把他的茅台酒送同事朋友。下车时,我当着他的面,把两瓶茅台酒给了司机,他并没有说什么。
医疗待遇是干部待遇非常重要的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经有文件,规定某些资历的干部可以享受副部级或者部级的医疗或者住房待遇,通常被称为单项副部级待遇,可以由自己做出选择。如我曾经担任秘书的武少文部长,夫人“文革”前曾是省财政厅长,根据文件可以享受单项副部级住房或者医疗待遇,因为家里住房已经是部长的房子,就自然选择了副部级医疗待遇。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后来的医疗待遇,很难说得清楚是什么级别。他的医疗关系仍然在北京医院,与原来当副总理时没有什么变化。按照当时卫生部保健局的通俗说法,他的医疗保健属于“200号”范围。“200号”是指正部长以上全国约有200人,这个范围的人员由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医疗费用。但是,在200号之内的医疗待遇有何差别,如部长级和“副国级”如何区别,“副国级”与“正国级”如何区别,甚至同为“副国级”之间是否有区别,这些都涉及更具体的医疗条件以及相应费用问题,非局内人并不清楚。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开始推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经常听到的离退休干部原则是: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因为官员通常都不愿意离开岗位,需要用这种条件作为激励。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原则的准确出处。一般来说,“生活待遇”是比较清楚的,主要与具体的生活条件有关。“政治待遇”所指何事,似乎不那么清楚。对于离开了领导岗位的人来说,不论是退到二线,还是正式办理离退休,具体的领导职权就没有了。对高级干部来说,没有了领导职权的政治待遇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我的观察来说,主要就是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知情权,说得更有力点,也可以算是一种参与权。这种参与权的具体形式,就是开会的待遇和看文件的待遇,更集中地表现在看文件的待遇。
纪登奎退出领导岗位后的政治待遇,显然我不可能全面了解。因为,他与中央高层还有一些单独联系,我们九号院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更不参与。从我所知道的参加会议情况看,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重要会议了。一般来说,退休官员开会的待遇大概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礼节性的会议,纯属待遇问题,比如中央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新年茶话会、国庆观礼等等,通常是按照官员级别划定邀请范围,象征了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是履行知情权的会议,如传达会议文件和高层领导人讲话,或就某些问题听取一定范围老干部的意见。一般来说,会议传达到哪一级别,与文件阅读到哪一级别,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会议和文件,可以口头传达到一定级别干部,但要求不准记录。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参加的会议主要是农村政策的讨论座谈。在我的印象里,中央高层研究制定政策的会议,他没有正式参加过。
对于高级干部来说,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待遇,或者说是体制内政治信任的基本指标。在现行体制中,看文件的级别和范围,可以说是除了实际职权外最重要的权力,或者说是实际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党内文件都有发放范围或阅读的级别规定,一个干部可以看什么级别的文件,直接显示其政治地位。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之后,看文件的级别显然是部级,并且在部级干部的文件传阅中,排序也不在前边。在他前边的,是现职的部长级干部。当年的九号院机构里,部长级干部有十五六位,看文件的基本顺序是,现职部长级干部为第一顺序,非现职(或无领导职务部级干部)为第二顺序。在现职部级干部中,看文件按照排名顺序。如果同样的省部级文件有两份,则现职和非现职同时开始传阅,如果只有一份,则是从现职部长中根据排名开始传阅;现职部长传阅以后,非现职的部长开始传阅。有的机密文件,或者有传阅时间要求的,或者是不适宜秘书人员阅读的,通常通知本人来机要室阅读。部长本人到机要室看文件,则不怎么讲究排名顺序,先到者先看,后到者后看。通常情况下,高级干部阅读文件可以在办公室,也可以在家里。根据规定,送取文件不得使用公共交通,也不能骑自行车。那时候,我送机要文件,或者是单位派出专车,或者是领导的司机来单位里接。
通常情况下,不是因为开会或者到机要室看文件,纪登奎并不来九号院。大部分文件是送到他家里去,他在家里看完后再退回机要室。纪登奎在辞职后,直到来九号院之前,看文件是什么待遇,我不得而知。高级干部看文件的范围,并非机要人员确定划分。如果降低了某位高层领导人的文件阅读级别,一定是在高层内部有批示规定。李文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胡耀邦辞职后看文件的待遇变化。李文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担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在《我与胡耀邦的交往》(见《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中谈到,1988年秋天曾去看望辞去总书记后的胡耀邦。“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时常陷入沉默。”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辞去总书记的胡耀邦,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说到好多文件已经不给他送了,显示高层看文件仍然有很多范围的规定或区分。
有些文章说中国是“文件治国”。当然,文件治国比“最高指示治国”、“批示治国”要进步很多。因为文件比领导“指示”、“批示”更具有规范性、公开性,所以具有较多的现代政府运行的特质。但是,“文件治国”与“法律治国”比,显然要逊色很多,因为法律具有更多的规范性、公开性,也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与政府工作比较,党内工作对于文件的依赖更加严重。对于党内高级干部来说,控制阅读文件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控制一个人参与政治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个意义上,阅读文件的权力,是党内官员的基础性政治权力,阅读文件的范围直接决定于政治地位的高低。
(三)
综合来看,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长级范围内的。问题在于,他从副总理位置上发生的这种待遇变化,并没有看到文件依据。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的工作安排的内部文件,也没有看到高层领导关于他的待遇问题的批示。据说,高层有口头传达,说纪登奎享受正部级待遇,但并没有准确出处。我们同事间曾经议论,他的这种待遇变化,虽然没有公开文件规定,如明文规定其级别从副总理级降为正部长级,但是,一定有某种来自最高层的官方依据。这种依据可能是某个高层领导人的批示,而这种批示不在党内和社会上公布,甚至在党内高层也不正式传达,仅仅是批示给有关人员执行。
高层有一种比较正规的说法:纪登奎在文革中有“严重政治问题”。但是,高层对于纪登奎的组织处理,显然与另一种犯错误官员的处理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九号院曾经接收过一个受到撤职处分的部长,即原林业部部长杨忠。杨忠因为黑龙江兴安岭大火灾受到处分,被撤销部长职务,行政级别从正部级降为正局级。他来到九号院,待遇问题很清晰,一切按照正局级安排,并被安排担任一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一个相当于司局的单位。杨忠的处理,从官场程序而言,经过了国务院的公共议程,有明确的规则,有明确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的规则和错误,在形式上,处分是完备的。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连表面上的处理规则和是非标准也无法确立,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处理和说法,似乎没有任何一项错误可以彻底追究。因为责任是理不清的。这种情况显示,党内组织处理的制度化水平不高,随意性很大,不仅对于社会没有公开性,而且内部的程序和规则也不清晰。
为什么高层对纪登奎的处理语焉不详?或者说,没有明确的处分,但给予了某种惩罚。当时,九号院一些高级干部时有议论,基本说法是,纪登奎的问题实在复杂,不那么容易处理。不明不白降了级别待遇,其实有深层隐情,就是他的错误也是有些不明不白。虽然,纪登奎在高层十年间,得罪了不少人,积怨甚深甚众。但是,从党内处理来说,难以通过正式程序给以明确说法。所以问题不明不白,降级也是非正规进行。为什么纪登奎的错误难以处理,因为这些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系在一起,也与当时还在位的李先念等若干领导人纠结在一起,无法往深处追究,否则,会牵扯到更加复杂难办的人和事。也就是说,纪登奎的“严重政治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清算的。
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清算,是国际范围内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过往政治领导人的清算处理,因为历史事件和政治责任的复杂性,采取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办法,也是一种无奈之中的明智之举。具体到纪登奎,如果真要把他的错误和责任梳理分辨清楚,那就不是如何对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披露和梳理一个时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认定的事件及其责任,也不是一个人,而是直接关乎众多领导人的历史责任和道德形象,也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整体形象。
Visits: 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