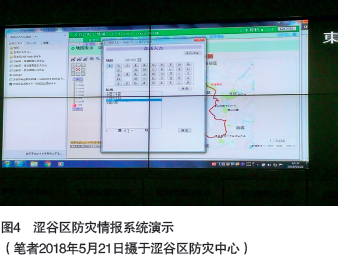丛晓男 朱承亮
日本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地壳运动活跃, 地震灾害多发。为增强城市抗震能力,降低地震及次生灾害损失,日本很早就建立了系统化的地震防灾减灾机制。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的大地震(“3·11”地震或东日本大地震),造成了死亡近2万人、毁坏房屋32万多栋的惨重损失。在震后的数年里,日本各界开始反思此前建立的防灾减灾机制的弊端,并作出针对性改进。
2018年5月,笔者有幸遴选为日中植树造林国际联合事业2018年度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的团员,随团赴日本开展了为期8天的实地调研。日中友好会馆会长、日本参议院前议长江田五月接见了代表团一行。此行重点考察了日本“3·11”大地震后的防灾减灾进展。笔者访问了东京都涩谷区防灾中心,与涩谷区危机管理对策部防灾课开展了深入交流;访问了东京大学综合防灾信息研究中心和东北大学灾害科学国际研究所, 分别听取了日本学者关于防灾机制建设和灾后重建的最新研究进展。此外,还深入东日本大地震受灾核心区仙台市、石卷市、气仙沼市、松岛地区等,同当地的地震亲历者、救灾公益社团法人、政府防灾中心等进行了交流座谈,详细考察了这些区域的受灾过程、灾害应对及灾后重建情况。调研过程中,日本地震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认真研究、借鉴日本灾害应对经验,对提升我国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对此次调研中发现的日本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进展进行了梳理,并对我国防灾减灾能力的优化方向进行了思考。
日本地震防灾减灾进展
(一)法制的修订与补充
日本高度重视防灾减灾立法工作,已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其中,《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防灾减灾的基本法,是为实现灾害法制的体系化、增强灾害应对的系统性而制定的法律。按照灾害类型, 日本的防灾法律又衍生出针对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风灾、水灾、滑坡塌方泥石流、暴雪、核灾难等不同类型的专门法;按照灾害应对环节,又可将法律分为预防阶段、应急阶段、重建复兴阶段三种类型。日本建立了“灾害追加型”的法律修订补充机制:在发生较大灾害后,及时发现现有法律漏洞,然后加以修订和完善。这种法律制定机制就像“拼花图”一样,使法律体系不断健全,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东日本大地震后,针对灾后交通恢复、物资供应等环节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日本东北大学等机构的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法律修订建议,重点加强了灾害应急方面的条目。例如,在道路疏通方面,建议将道路管理者纳入到疏通主体当中,从而使地方政府成为道路疏通的主体(针对《灾害对策基本法》第76条之6);在道路修复方面,当大范围、大规模灾害发生时,建议由国土交通大臣而不是原有的地方警察体系主持修复道路,从而明确了中央政府在重大灾害中负有的交通修复职责(针对《灾害对策基本法》第74条之3、第78条之2);在救灾物资供应方面,鉴于东日本大地震后存在灾民长期居住在避难所的事实,建议将“临时住宅”“应急修理”等字样删除(针对《灾害救助法》第23条),以解决避难生活长期化问题,针对物资供需不匹配问题,建议运用市场机制来提高供需匹配度;在灾后重建方面,建议制定“灾害重建法”,以改进对中长期受灾者的救助机制,并为灾后重建和复兴建立可靠的制度框架。
(二)防灾教育理念的转变
日本国民从小就接受系统的防灾教育,内容全面、形式多样, 国民更是积极配合。日本将逃生技能列为幼儿必修课,教育省规定, 每个学期学校都要开展防灾演练。对于这一政策规定,每个学校都能加以认真落实,中小学经常组织自救演练,让国民从小就有应对灾害的心理准备和必要的自救常识。此外,日本将每年的9月1日确立为“全国防灾日”,藉此让每个国民熟悉防灾知识,提高灾害应对能力。日本还特别重视防灾教育和防灾训练基地的建设,为市民和参观者提供良好的防灾教育和培训空间,地震模拟体验装置得到普遍应用,以逼近真实地震场景(图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防灾教育的重点有所转变,即从“灾后爱心教育”转变到“灾难中生存教育”,并且要遵循三项原则:一是不能完全相信“预测”,因为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尚不能“预测”到预想不到的因素,“预测”往往会束缚人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在地震及其导致的次生灾害面前,人类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和准备来迎接自然的挑战;三是主动避难,灾害中特别是海啸灾害中的第一要务是确保自身安全,必须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向他人施救,避免出现家人朋友之间相互寻找而丧命的悲剧出现。
(三)防灾减灾工作的精细化
追求细节是日本国民的典型性格,这种性格也渗透到灾害应对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法律制定,还是个人求生指南,都必须细化到可操作的程度。此次调研,可从三个方面管窥日本防灾减灾工作的精细化程度。一是灾害情景分析的精细化。防灾中心通过实地摸查,将城市所有房屋的地震抗毁性数据、居住人口等数据搜集整合起来,再通过计算机模拟方法对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地震所造成的损失进行情景模拟,从而构建了精细化的灾害损失评价系统。以东京都涩谷区为例,在发生首都直下型、烈度6 级地震的情景下,可模拟出损失结果为死亡250人(夜间常住人口的0.12%)、受伤5000人(夜间常住人口的2.4%)、建筑物完全毁坏5800 间(区内建筑的15%)。此外,还可对城市管线受损情况进行细致分析,从而估算出包括电力设施停电率、通信设施中断率、燃气设施停供率、供水管道设施断水率、排水管区受灾率等一系列细化结果。二是防灾演练的精细化。日本防灾演练的原则是知行合一,书本上的防灾知识必须要在演练中加以实践, 紧急避难场所上均清晰印有避难逃生标志(图2),演练中需要亲自走过一遍,可以说这种演练已经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三是救灾物资储备的精细化。日本既注重救灾物资的标准化设计,又充分考虑到了灾民的个性化需求。以涩谷区为短期灾民提供的应急食品为例(图3), 该食品保质期长达3年,包含27种食源,能够充分保证灾民营养均衡, 过敏体质的灾民也可放心食用而不会产生过敏情况。
(四)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信息化
日本高度重视前沿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地震防灾中的应用, 已经实现了地震应对的高度信息化。在防灾教育和培训方面,大量采用虚拟现实技术,真实还原灾害现场,在灾后现场实地教育中,还采用了最新的增强现实技术对比观察同一地点在不同时期的景观变化情况。在灾害损失模拟方面,构建了精细化的灾害损失多情景模拟平台,能够在不同地震情景下,开展损失预先评估,为防灾救灾提供了有效的基础支撑。在防灾信息发布方面,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框架,集成了高分辨率监控探头、实时通信技术等,建立了“防灾情报系统”(图4),灾民可以通过手机、P C 等不同客户端登陆该系统,了解最新的地震灾害情况,并通过监控探头寻找安全的避难所。此外,建立了包括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地震专用频道广播、雅虎地震情报等在内的“紧急速报系统”,也可以实时提供灾害信息。中心机房还配备有紧急发电装置,当电源受到地震破坏的时候,可以为中心机房提供持续不断的电力。在灾后舆论监测方面,日本开展了“灾害信息论”学科研究,对灾后谣言传播、舆情引导、声誉危机等开展了广泛分析。
(五)“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救援机制
日本构建了包含家庭、社区和政府在内的多主体协同防灾减灾救灾机制。不同主体各有分工、相互协同。家庭负责做好自救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家庭内部储备足够的物资、提高自家住宅的抗震性、采取措施防止家具等物品翻倒、确认避难所位置和逃生路线、保持家人之间的联络等。社区主要负责做好互助工作,包括加入自主防灾组织、帮助老年人及残障人士、参加社区防灾演练等。政府负责做好公共救助,政府工作人员要加入到灾害对策机构、各避难所、医疗救护所等组织中去,与市民和相关机构(包括警察、消防、自卫队、公共交通、城市管网等)开展联合救灾。不同于中国政府部门在灾害救助中所发挥的支柱作用,日本政府的主导力量相对稍弱,更加注重采取“自下而上”的灾害救助方式,即将做好个人和家庭的自救行动作为灾害救助的基础。由于防灾教育中时刻体现这一理念,日本国民本身形成了较高的自救能力。然而,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有意加强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救灾中的主导作用,即采取“补充性原则”,按照“个人—家庭—地区社会组织— 市町村—都道府县—中央”的排序方式,当下级单位不能履行其职能时,要求上级单位必须介入救灾, 从而在保持“自下而上”救灾能力的同时,强化了“自上而下”的救援方式,有利于发挥上级政府在大范围、大规模灾害中的能力。
(六)社会力量在防灾减灾中的角色转变
日本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N G O)、非营利组织(N P O)在灾害救助中的作用。东日本大地震后,社会救助力量的作用得以进一步强化。在对日本公益社团法人“Future Support石卷”进行调研时发现,志愿者、NGO和NPO在与政府部门联手构建援助计划、物资分配、地毯式搜索、淤泥瓦砾清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在救灾过程中也出现了彼此身份不认同、信息沟通不畅、救灾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 其作用也逐渐从紧急支援过渡到辅助支持。有鉴于此,志愿者和NPO成立了“石卷临时住宅自治联合推进会”,对政府提供的灾后公营住宅展开社区支持,政府则开始给予财政支持并逐年增加拨款额,从而使该组织获得了高度信任,成为国家灾害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弥补了政府援助的局限性,发挥了互助共助的重要作用。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高度集聚导致灾害暴露度骤增,防灾减灾任务十分艰巨。尽管当前我国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防灾抗灾要求,防灾立法、防灾教育、防灾精细化、救灾主体协作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尽管我国的自然灾害种类同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日本在地震灾害应对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我国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是完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防灾减灾法律体系建设,既能够为防范自然灾害风险提供法制依据, 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防灾减灾救灾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仍存在三个短板。一是防灾基本法仍然缺位,导致各项防灾减灾法律法规的制定缺乏共同的法律基准;二是现行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多围绕具体灾种制定,仅限于防洪、抗旱、地质灾害防治、防沙治沙、森林保护等少数几个方面,法制不健全、体系碎片化的现象比较突出;三是尚未建立起防灾减灾法律法规的动态修订机制。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应尽快研究制定减灾防灾基本法, 围绕该基本法逐步修订补充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灾种为分类基准,形成体系化的灾害应对法律法规;引入“灾害追加型”的法律修订补充机制,在重大灾害发生后,要及时分析法律漏洞,及时给予修订完善。
二是强化防灾减灾教育力度。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教育还比较落后,未能系统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国民大都缺乏危机意识和有效的实际演练,面对灾难时手足无措,仓皇跳楼致死和逃生踩踏事故等悲剧时有发生。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不强、自救互救水平不高等迫切现实问题,可以积极借鉴日本经验,尽快将防灾减灾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应从儿童阶段开始进行防灾减灾教育,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长效机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普及灾害应对知识;建设和完善防灾自救演练场馆与演练设施,切实开展防灾演练,做到防灾、自救业务的熟练掌握,提升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三是提升防灾减灾工作的精细化程度。我国防灾减灾的各个环节普遍存在精细化程度不足的问题, 导致灾害应对行动缺乏可操作性, 严重影响减灾救灾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学习日本的精细化理念,强化减灾防灾的可操作性和应对预案的实用性。一是要充分预估各类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并开展灾害损失的多情景分析,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灾害种类、发生概率、损失情况进行精细化分析,以此作为制定应对预案的基本依据;二是要进一步增强灾害应对演练的精细化, 对明确灾害应对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细节问题,细化相应的应对流程,并通过防灾减灾教育演练落到实处;三是提高防灾物资准备的精细化程度, 精准分析受灾者的各类需求,以此科学筹备救灾物资。
四是加强防灾减灾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我国灾害应对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大灾面前,仅通过纸质地图等传统介质指挥救灾的情况并不鲜见。应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手段在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灾害信息发布与预警、灾害应急指挥通讯、防灾演练模拟等关键信息化建设。灾害信息发布与预警方面,要强化灾害预警能力,提高灾害信息发布的即时性,使受灾者能够通过多种信息化渠道快速获取灾害预警信息;灾害应急指挥通讯方面,应加快构建公用应急卫星通信系统,加强卫星应急专网的统筹规划,并在灾害多发易发地区和重要城市、设施周边建设超级基站,提高应急通信网络抗毁能力;防灾演练模拟方面,要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建设一批先进的模拟演练基地。
五是构建多主体协同的防灾减灾机制。我国防灾减灾机制的优势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协调指挥能力, 这种“自上而下”的灾害应对机制是我国有效开展防灾减灾工作的基本保障。相对日本而言,我国受灾者、受灾家庭和基层组织的防灾减灾意识明显偏弱,自救、互助工作能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此, 应在巩固政府防灾减灾组织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自救、互助意识,提升其防灾救灾技能,构建包含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在内的多主体协同的防灾减灾机制。
六是重视社会团体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汶川地震后,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热情持续高涨,在应急救援、物资发放、心理抚慰、款物捐赠、灾后重建和社区减灾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协调联动、共同应对的救灾工作格局。然而,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仍存在组织无序、规范化程度不够、政策引导支持不足等问题。我国应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治理,扩大防灾减灾的底层基础。同时,应加强对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的培训、引导和调配,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参与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信息集成与动态模拟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Visits: 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