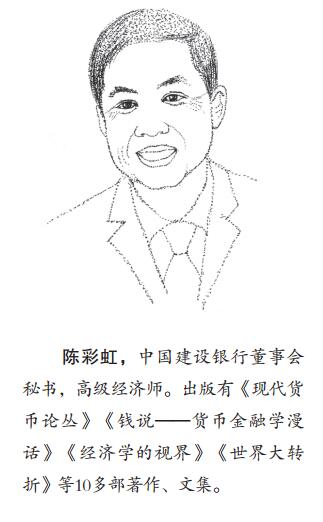陈彩虹
不少学者认为,制度比技术更重要。理由是,制度具有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和影响人的行为久远等特点;技术的作用则相对狭窄,就事论事的多,时空影响受限。这是颇有些道理的。譬如,用一种技术手段来禁烟,如用电子模拟烟替代真正的烟草,通常只能解决很小群体的问题;以法律制度禁止吸烟,面广势强,效果会要大得很多。基于此,重制度一直就是学界的主流看法。
不过,从公司治理的实践来看,很难说制度和技术哪个更重要些。这是因为对于治理目标而言,制度也好,技术也罢,都只是工具,而工具之间是无法直接比较优劣和重要性的。它们只有针对不同的治理需要,选择哪个工具更合适一些的问题。这有点如同挖掘机和铁铲,大致来看,当然前者厉害;细想下来,还真说不得哪个比哪个强——挖掘机挖土的效能大,却对付不了边边角角的地方。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应当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这种源自实践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公司治理领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都是如此,那么,主流的“制度比技术更重要”之说,恐怕要被改写的。
人所共知,别看我们天天都在使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词,真要给出它们明确的定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公司治理的意义上,我们将技术定位于针对具体问题而运用的技巧性方法,它通过改变具体问题中对象的物理或化学性能来实现其功能;制度则是针对相对普遍性问题而确立的规则、要求、程序等,它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来实现其作用。或者换种哲学式的说法,技术主要是针对具体问题中的“客体”而采取的办法,核心是作为对象的“物或事”;制度则主要是针对普遍问题中“主体”来确定的一般行动准则,重点是处在主位的“人”。
就上面的禁烟来说,技术手段禁烟,直接改造的是烟这个“对象”,让吸烟人吸不到真正的烟草;制度手段禁烟,则是警示人这个“主体”吸烟对社会、他人和自己的害处,并以惩罚的规则来迫使吸烟者调整行为,放弃吸烟。
这样的定位,虽然说不上完备和精确,却让我们对“技术”和“制度”有了较清楚的“实用性”区分,使我们能够针对不同问题,构建治理的合理原则,更有效率地选择运用不同的工具。这就是,对于那种改造“客体”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好采用技术工具;对于那种需要人们调整行为方式才能解决的问题,则最好诉诸于制度。粗略地讲,前者“对事不对人”,而后者“对人不对事”。
公司治理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里重要的既有“问题”一方,还有“导向”一方。先从“导向”来看,应当是包括导引出最合适的工具在内的。观察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大多有着“技术”和“制度”工具运用非常得当的经历。显而易见,用相配的钥匙去开相应的锁,用最合适的工具去解决相关的问题,达到的效果自然是会最优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问题”。公司治理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们“技术”和“制度”的视角下,这些“问题”可简化为“客体(物或事)”和“主体(人)”的问题两个大类。值得关注的是,在治理实践中,一旦“问题”出现,治理者通常会先选择运用“技术”工具去尝试解决问题,而不是马上想到和运用“制度”。这是因为,“技术”工具使用起来相对直接、单纯,只涉及“物或事”的对象,不会带来人的行为大调整,因而不会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急剧变化、紧张和冲突,可以用较小的成本,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实践理性”。它告诉我们,“技术”工具有自身显在的优势,并且不可能轻易被替代。
由此推论,“制度”工具一般是在“技术”工具无效,或虽然有效但解决问题有限的情况下,才出场的。鉴于“制度”工具的核心,在于直接调整“主体”人的行为,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一经登台,就会产生普遍的、强烈的和持久的反响。正因为如此,在公司治理中,这种“制度”工具的运用,通常是以“体制或机制变革”的面目出现的,属于重大治理事项,要耗费较大的成本。大致看来,这种“制度成本”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的设计和制定或修改成本,二是制度的执行成本,三是制度执行带来的其他附加成本等。而且,新制度的运行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期解决“问题”的目的,是需要一定时间来检验的。这样一来,耗费较大成本还无法快速确定效果的“制度”选择,就引出了“实践理性”的另一面:人们通常不会轻易地选择“制度”工具去面对“问题”。
因此,公司治理实践中先“技术”后“制度”的工具选择顺序,实则揭示了非常重大的治理原理——“技术”是日常的治理工具,应当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制度”则为长治久用的治理工具,应当追求相对稳定,不宜轻言调整和改变。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多改变的,是改变“客体”对象,而不是人与人关系的频繁调整。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技术”比“制度”还重要。至少,也是一样重要。
举例说,一遇到上下班迟到早退类问题,大多数公司首先想到的是运用“打卡”类的技术工具,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选择。一遇到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治理者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全量地、实时地获取各个层面的信息,保证及时合理地做出管理和执行的决策,当今许多公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实时监控”、“数据集中”等做法便是证明。即使是遇到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调整的普遍性问题,需要运用“制度”工具,如财务资源配置、成本分摊甚至于个人奖惩,很多公司也常常会考虑某些“灵活性处理”,如不动“存量”而只进行“增量”调整,或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则”,将问题涉及面缩减到最小的范围,也就不需要对整个制度和机制进行“推倒重来”的变革,减少不必耗费的“制度成本”。
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工具的“对事不对人”,并非完全“不对人”,而是通过对事的处理,渐进地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同样,“制度”工具的“对人不对事”,也不是完全“不对事”,而是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去实现解决“事”的问题。“打卡”最后的目标,是培养人们的时间和纪律观念,改变迟到早退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资源配置和奖惩制度等的出台,是直接激励人们去调整行为,理顺人际关系,促进业绩提升,实现治理的有序、有效。可见,全面地理解“技术”和“制度”工具,应当从改变“客体”之事,同时又改变“主体”之人两个方面去认知——“技术”是由事而人,“制度”则是由人而事,它们都关联“事”和“人”两个方面的。毫无疑问,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是这两种工具共同的、根本的目的。
从改变“人”的角度出发,“技术”和“制度”工具的不同,仅仅表现在前者是间接的、渐进的;后者是直接的、突变的。当治理中的“问题”出现时,依从于“实践理性”来选择解决工具,不只应当考虑两者不同的成本负担,还应当从“人”的行为变化上,考虑“渐进”或“突变”的效果和影响。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实践,一定是少不得精心选择和运用“技术”和“制度”工具的高超艺术的。
2015年6月,北京市开始了“史上最严厉”的公共场所禁烟制度。一年多过去了,效果不理想。从公司治理对于“技术”和“制度”工具的选择里,我们可以找到某种解释。这就是间接的、渐进的,同时又是成本较低的禁烟“技术”类工具严重缺乏;而“禁烟制度”执行的成本太大,大到完全无法全部负担,结果是“能禁多少算多少”。
Visits: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