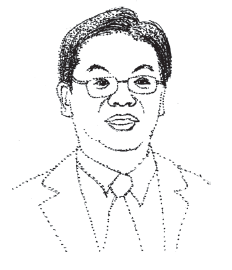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在中国社会秩序的背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超稳定结构”支撑着,它建立在一整套治国思想和治国制度的基础之上,体现着中国古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智慧。
家国天下
“治”,本是一条古水的名字, 它出自泰山,后引申为从水的初始处、细小处开始,进一步引申为对河流整修、疏导;“理”,本义是物质的组织纹路,引申为将山上挖来的璞石加工成美玉,使之成器,进一步引申为整理、整治。战国时,“治”与“理”开始合为一词并用于国家管理层面。如荀子说“明分职,序事业, 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韩非说“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治理”用于国家层面,一般指按照某种规则、制度对国家进行管理和改造,也就是从国家层面操作公共权力,通过管理社会事项来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很多理论上的探讨,也开展了丰富的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
提到治理国家,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考证,这句话最早出自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一书,虽有些夸张,但它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古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儒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国” 与“家”密切关联。《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具体内容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儒家构建出一个由“家”到“国”的基本框架,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儒家治国思想中,“家”与“国”始终是一体的。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意思是天下的基础是国,国的基础是家,家的基础是个人。荀子也说“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认为君臣的关系与父子、兄弟关系并无二致。在儒家看来,国家由家庭、个人所组成, “国”是一个放大的“家”,只有家和才能国兴。在家庭层面儒家强调忠亲孝悌,这些理念被直接引入国家治理中。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他认为君子对父母能尽孝道,就能将对父母的孝心移作对君王的忠心;事奉兄长知道服从,就能将对兄长的服从移作对长官的顺从;管理家政有条有理,就能将理家的经验移作处理公务。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人视家事即国事,在家中养成美好的品行道德,在外也必然会有美好的名声,美好的名声将流传百世,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倡行“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理念,当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会选择后者,以舍家报国、精忠报国为荣,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夯实了国家的根基。
“家国天下”的治国思想也有另一层内涵,那就是要求执政者要充分重视个体、家庭的利益。《尚书》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贾谊在《新书·大政》中强调“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认为“夫民者, 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中国古代的治政者深知,要实现“国泰”必须“民安”,必须以民生为念,必须以政惠民,所以在推行重大政策时通常都要考虑保民、富民、利民、恤民的原则,以使基业常青。
郡县安国
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主导, 从疆域范围上看,几大更适合农业耕种的平原成为人口聚居区,以这些平原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疆域的基本轮廓。由于早期人口不多,社会组织形式基本以“城市型”为主, 城与城之间通常还有着广阔的无人地带。在“城市型”社会治理中,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制度更容易得到实施,于是“分封制”成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后来人口逐渐增加,社会基本形态向“城邦型”演化,城、乡、村结合形成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区域性“大国”逐渐崛起,所管辖的面积更大,人口流动和人口阶层变动也不断增加,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考验。
“分封制”的特点是“划疆分治”,这种治理模式不利于各地区间资源和优势的互补,对内不利于调动各阶层活力,对外不利于形成整体合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这种模式显得越来越落后。战国时期的秦国推行综合性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壮大,通过对外兼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秦国意识到传统分封制作为国家治理手段已经落后,于是在新获得的地区改设郡县,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领导”,这一措施带来了国家治理制度的新变革,“郡县制”由此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一直沿用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郡县制作为国家的一种治理制度,其内容非常丰富,决不是在地方上设置一些郡和县那么简单。在郡县制下,国家从行政上管理郡,郡管理县,郡县的长官由国家任命。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些官员不能世袭,而由国家“择优选拔”,从而形成了一个技术型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力量,较之以往的世袭贵族具有很大的先进性。由于农业经济所涉及的领域并不复杂,所以中央层面设置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即可管理国家,使行政资源实现最大化节约。在对百姓的管理上, 郡县制下还有“编户齐民”制度,尽管各朝代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核心是共通的,那就是使人与社会、人与土地紧密联接在一起,形成“人不动、户不动、地不动”的基本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固然有僵硬的一面, 但对以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却是适合的,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社会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郡县制以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有效协调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保证了中央集权,对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史记》说“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 天下无不治”。郡县制成型于秦汉, 隋唐时改郡为州,宋元时在州以上增设路,明清时郡级行政单位多称府、府以上增设行省……管理形式虽不断变化,但郡县制的核心没有变。郡县制盛行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随着郡县制的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的能力随之增强,困扰许多封建王朝的地方割据问题也就慢慢消失了。
以礼治国
秦汉时期的郡县制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政权延伸至县以下,县下设乡,乡下还设有里、什、伍等组织。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县下设乡的规则是:“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秦汉时期乡的负责人称“有秩”或“啬夫”,管理一乡;里的负责人称“里魁”,管理百户左右;下面还有“什主”“伍主”,分别管理十户、五户,他们的职责是“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后来人口和郡县数目都不断增加,如果按照这样的治理思路继续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无疑会空前庞大,如何更有效、更节约地解决基层治理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礼治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乐记·乐论》认为“礼者, 天地之序也”,《左传》认为“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说文解字》解释“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早在西周之前礼制就形成了,体现为一些固定的仪式、程序和规范,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一定权威性。严格来说,“法”其实产生于“礼”, “礼”中的一部分规范升级为强制性约束便成为“法”。具体而言,在夏商周时期“礼”与“法”还融为一体,“法”存于“礼”中;到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当时的一些治国理论强调了“法”的优先性和重要性,主张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法”无法完全替代“礼”,社会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大量的社会行为无法写入法条, 所以汉代董仲舒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在董仲舒看来,“德”不仅不能被“刑”所取代,而且“德”是“阳”,“刑”是“阴”,“德”处于先导位置。随着儒家理论被逐步确定为治国的核心思想,各代统治者们都更加重视德治、礼治的作用,通过其教化作用在潜移默化间对法治进行有力补充。清代淩廷堪在《复礼》中对礼治的作用有如下总结:“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其秀者有所凭而入于善,顽者有所检束而不敢为恶。”
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在国家治理层面,实现了相互包含和交叉重合的综合治理模式,不仅消除了治理上的空白点,而且那些“礼”和“法”都加以强调的地方往往就是国家治理的难点与重点,使得国家治理的目标更加突出,基础更加坚实。
秦汉以后礼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尤其在基层治理中,礼治发挥了其对社会个体、宗族巨大的渗透和影响作用,通过一系列道德构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层社会实现了“自治”, 国家的行政管理资源在县以下逐渐淡化甚至退出,出现了“皇权不下县”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的安全性、稳定性却没有因此削弱。
Visits: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