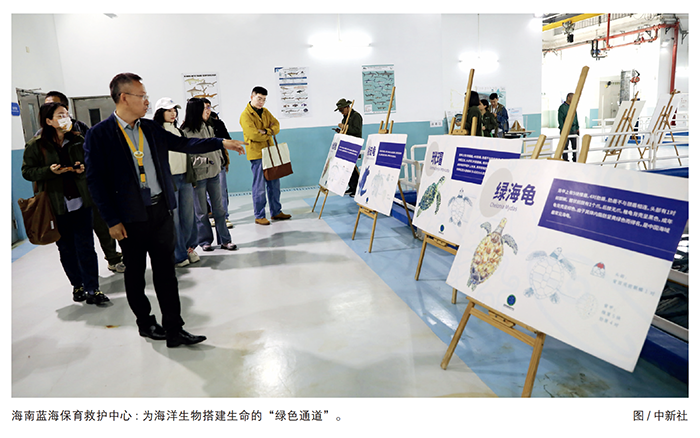李双建
内容提要: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新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将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海洋强国建设进入充满挑战的战略机遇期。国际海洋形势呈现安全趋紧、格局趋变、竞争趋热、保护趋严的总体特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海洋有效承载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源高效率利用、生态高标准保护、公众高品质生活、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本文认为应准确把握海洋资源开发保护的新要求,并提出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更加健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以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倡议和行动得到广泛认同,海洋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将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海洋强国建设进入充满挑战的战略机遇期。应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部署,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决策安排,准确把握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高质量发展阶段海洋强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提升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水平,加快构建蓝色发展新格局。
海洋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全球海洋治理正在经历一段孕育机遇但充满矛盾斗争的调整过程。各种海洋利益复杂交汇与冲突,各类涉海关系相互作用与影响,推动海洋国际关系从“合作中竞争”转向“竞争中合作”的新阶段,贯穿“十四五”“十五五”甚至更长时期,国际海洋形势呈现安全趋紧、竞争趋热、格局趋变、保护趋严的总体特征。
(一)周边海洋安全风险和矛盾交错叠加
海洋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海上方向战略压力和安全风险持续加大。美国加快实施“印太战略”并组建海洋联盟,利用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手段拉拢有关国家,在我国周边频繁制造海上事端,给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带来挑战。总体来说,和平与发展虽然仍是时代主题,但海洋日益成为国家间利益博弈甚至冲突的主要领域,未来海洋“灰犀牛”“黑天鹅”事件风险加大。需坚持底线思维, 提高妥善应对和系统性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
(二)海洋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日益加剧
海上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之争。第四次科技革命为全球海洋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深水、绿色、安全”领域海洋科学研究成为热点,一些海洋关键技术装备已呈现革命性突破先兆。但美西方对我国科技封锁和海洋产业压制持续升级,一方面,发达国家争相获取海洋观测、海底通信、海洋能等领域的先发优势,并对我国掌握深潜器、新型传感器等技术高度戒备;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西方持续推行对华产业链“去风险化”,我国海洋产业发展将会持续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压制”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
(三)海洋治理体系和权力之争愈发凸显
全球海洋治理关键领域国际规则正在酝酿,迎来新型国际海洋秩序构建的重要窗口期,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规则加快落地,深海采矿、北极航行等新规则呼之欲出,蓝色经济、蓝色碳汇、海洋限塑、渔业限捕和公海保护区、南极管理区等治理进程加速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制度性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对我国遂行国际义务、倒逼国内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酝酿形成国际海洋新秩序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海洋治理体系, 意图以“美式规则”主导国际海洋秩序,限制和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海洋国家。
(四)海洋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基本共识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应对海平面上升、海洋低氧酸化、海水变暖和保护海洋资源等诉求突出,发达国家则以“保护”之名行争夺和控制海洋之实并占据道义制高点,这种极端环保主义政治化将给我国海洋发展和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例如, 美西方着力推动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到2030年需新增海洋保护区域面积约8300万平方公里,借此推进全球公海保护区建设,对我国国防、经济、能源、资源等战略利益和海洋权益产生潜在影响。
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面临新要求
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海洋有效承载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源高效率利用、生态高标准保护、公众高品质生活、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海洋开发保护制度体系建设需求更为紧迫,对推进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一)海洋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
当前沿海地区发展海洋经济热情高涨,沿海城市带、现代海洋城市和海洋产业园区成为海洋经济发展要素的主要集聚空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依海”特征更加明显。随着“一带一路”海上合作进入深耕阶段,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赋予了海洋经济更深刻的发展内涵,并对海洋经济优化调控方向和政策导向提出更高要求。同时,近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海洋产业南北方之间、区域板块之间分化扩大,也给海洋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能带来更多挑战。
(二)海洋科技自主创新仍面临压力
与发达海洋国家相比, 我国战略性、基础性、颠覆性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海洋产业发展相关的基础研究水平总体不高,尤其在深水、绿色、安全等海洋高技术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原创性和高附加值创新成果较少,核心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问题还比较突出,科技发展主动权掌握不牢。在高端船舶和海洋装备制造领域,国际供应链主导能力不足,多以集成制造为主,大量核心技术和关键配件需要依赖进口。各类极限海洋环境下潜水器耐高压结构和低密度浮力材料、深水钻机、全功率谱系船用低中高速发动机等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海水淡化国产反渗透膜、高压泵、能量回收装置的关键性能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
(三)海洋资源利用的刚需与生态保护的压力并存
实现既顺应海洋开发愿景、又守住海洋保护底线的双重目标,亟须健全精细化、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做好海洋资源利用的增量控制、存量挖潜、减量消化, 努力实现海洋资源的开源节流。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沿海地区资源约束趋紧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区域人口密集、产业集聚、资源需求多、环境压力大,能源、矿产、水等资源要素缺口较大,海洋能、深海稀土、淡化水等海洋资源补充接续甚至主体供给地位显现,低效益、粗放型的开发利用模式难以为继,海洋资源供需矛盾和优化开发利用问题亟待破解。同时,高强度海洋开发利用造成的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问题突出,近海环境质量不佳、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依然存在, 海岸带生态环境约束持续加大,致使海洋资源允许开发的类型与总量明显压缩,获取难度与成本有所上升。
(四)近海空间资源紧张催生深远海开发利用需求
我国近海开发过度与深远海关注不足形成强烈对比, 90%的开发利用活动集中在潮间带和水深15米以内浅海域, 造成行业用海冲突、生态系统受损等问题。随着近海开发空间趋紧、生态约束增强, 相关行业及沿海地方逐步将海洋空间利用转向深远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深远海空间开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利用活动主要以油气勘探开采、国际光缆铺设施工为主,且我国对国管海域、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区域的海洋资源本底掌握不清,未形成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链条, 已产生无序无度利用的苗头性问题。
(五)海洋承载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多元
随着沿海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人民群众在生命财产安全、海产品供给和海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民生诉求不断高涨,对海洋所承载的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多元,优质海产品、特色亲海空间等个性化、高品质民生需求明显上升。新时期,满足公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成为海洋资源开发从抓好保护到提升品质的关键。要更加注重海洋强国建设的民生领域问题,针对当前公众切身感受、反映突出的海洋领域“痛点”和“短板”重点施策,有效保障国家能源、食物、水资源等安全,保障公众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的亲海权利, 保证优质海产品持续稳定供给,着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对海洋强国建设的获得感。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构建新时代蓝色发展新格局
总体来看,我国海洋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将发生复杂而深刻的重大变化, 海洋强国建设将进入充满挑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这既是海洋外部矛盾风险的交错叠加期和海洋治理秩序构建的重要窗口期,也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推进期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攻坚期。新时期推进海洋资源开发保护,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开发与保护两种关系,坚决贯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牢牢把握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陆海统筹,推动构建蓝色发展新格局。
(一)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
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推进落实《海洋环境保护法》《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推动《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健全海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完善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围填海管控、海岸线保护、海域和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海岸建筑退缩线等制度。制定海水淡化、海洋能规模化利用政策。探索制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用海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实施严格的海域海岛海岸线用途管制。严控围填海, 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鼓励地方探索与土地利用衔接的存量围填海管理机制。对无居民海岛以保护为主,实施“清单式”管理。引导海水养殖、海上风电等产业向远海发展,支持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储近用远”。有序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及行业、民生用海用岛,明确用途管制要求和转用规则。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和岸线分类保护制度,制定占用岸线准入清单,严格管控建设项目占用自然岸线。
实施精细化用海管理。在保障用海人权益的前提下推进立体确权,制定海域综合利用和立体开发政策。建立闲置海域使用权、无居民海岛资源收回制度以及节约集约用海用岛标准体系,出台行业用海用岛面积控制标准。深化海洋空间详细规划研究和试点。开展单位海域(岸线、无居民海岛) 资源效益产出评估,建立海洋空间资源低效利用退出机制。制度化开展海洋资源调查,摸清海洋资源家底,夯实精细化用海管理数据基础。
(二)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
构建海洋保护地体系。针对尚处于保护空白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和濒危、珍稀物种的集中分布区,选划建设海洋保护地,根据各类海洋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和物种栖息、迁徙规律,构建海洋保护地网络, 提升管护水平。研究建立国家海洋公园制度,探索在我管辖海域敏感区内设立国家海洋公园,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同时维护海洋权益。
推进海洋生态恢复和整治修复。持续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保育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海藻场等海岸带生态系统,建设生态海堤。加强赤潮、绿潮、外来物种入侵等海洋生态灾害治理。实施入海陆源污染物精细化治理,防治各类陆源污染、海上污染,提升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持续改善海洋环境质量。以严格保护和生态修复协同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健全生态系统碳汇监测网络,推动海洋领域增汇减排、碳汇核算交易,促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提升沿海地区人居环境品质。积极保障和拓展公众亲海空间,因地制宜打造环海绿道和滨海廊道,提升公共海滨浴场质量。塑造特色鲜明的滨海城乡风貌,对影响海岸带景观轴、天际线、山脊线的建筑设施等进行控制和引导。科学规划建设滨海旅游集聚区,保护修复和适度利用海洋自然遗产和文化,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海洋博物馆、海洋科技馆、海洋科普基地等文化设施。
(三)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形成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新布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依托,优化北部、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布局,构建定位清晰、层次分明的现代海洋城市体系,形成带动全球海洋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和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影响极。打造龙头企业引领、高新技术驱动、协作协同紧密的海洋产业集群,优化整合港口资源,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发展一体化、装备智能化、业态高端化的世界一流港口群,构建“东中西”联通的陆海国际商贸物流大通道,深化自由贸易港等沿海开放平台功能,促进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南北协调的开放新格局。
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一是推动海洋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捕捞限额管理和休渔禁渔制度,严控近海捕捞强度,推广深水远岸养殖,发展可持续远洋渔业。发展绿色养殖,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进渔业与休闲旅游等产业紧密融合。支持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储近用远”,提高自主勘探能力,保障海洋油气增储上产。推进港口绿色化、智能化、安全化升级改造。二是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大力发展高端船舶制造,支持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国产化,重点提升海洋油气、海上风电、深远海养殖、海水淡化和海洋能开发等装备制造的自主化水平。推动海水淡化和海洋能规模化利用,加快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化进程。
(四)加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着力突破海洋核心装备和关键技术瓶颈。围绕深水、绿色、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需求,强化自主海洋核心装备和关键技术研发。在海洋观测监测领域,重点研发新型传感器、无人智能平台和目标探测识别技术;在深海资源开发领域,重点支持深海科学、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调查勘探装备谱系化发展,提升装备模块化制造水平;在海水养殖领域,加大深远海大型养殖装备和生态化养殖技术研发力度;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提高豪华邮轮、智慧船舶、绿色船舶、极地船舶的设计建造水平;在海水淡化领域,重点支持高性能反渗透膜、能量回收装置等研发制造;在海洋能开发领域,突破发电装备关键部件设计制造、系统集成技术等瓶颈。
加强海洋科技储备与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持续开展海洋科学、极地科学基础研究,争取在海洋动力过程、陆海相互作用、海洋生态系统变化规律等方向实现原创性突破。聚焦海洋空间利用、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 构建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技术储备优势。同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场化服务, 扶持培育涉海中介服务机构和专业化技术交易平台。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建立海洋产业创新联盟,优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模式,建设一批海洋领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品制造研发中心。
(五)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提升深海极地治理能力。深度参与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保护、南极条约体系、北极治理框架等磋商谈判进程。加紧公海保护区、极地海洋保护区和南极管理区等问题研究。强化极地事务统筹协调和综合保障能力,优化极地观测站网布局,加快推进“冰上丝绸之路”。
巩固拓展蓝色伙伴关系。大力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制定蓝色伙伴关系战略框架与行动计划。丰富国际海洋公共服务产品, 发起海洋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计划,针对重点海域、围绕重点领域建立彰显“中国智慧”的区域海洋公共服务产品体系, 逐步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安全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规划、标准、方法、产品合作共享。
增强全球海洋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全面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引领地区和全球海洋治理规则建设,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联合国海洋可持续发展大会等多边合作进程和机制建设,在海洋气候变化应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防灾减灾、海上安全、极地事务等领域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和规范制定。努力扩大在涉海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支持相关国际组织在华设立机构。
(参考文献略)
作者为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Visits: 360